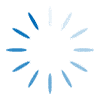第二天晌午,汤闻骞和龙娶莹又在老地方碰头——凤河街边那家二层的悦来酒楼,二楼靠窗的包间。
汤闻骞推门进来,手里捏着个信封,“啪”一声拍在桌上,力道不轻。
龙娶莹正喝茶,眼皮抬了抬,没急着问。
“退回来了。”汤闻骞一屁股坐下,手指点着那信封,“原封不动,银票还在里头。我派去的人说,丞衍接过去,拆开看了一眼,什么话都没说,直接塞回他怀里,转身就走。”
龙娶莹放下茶杯,拿起信封。封口没拆,她隔着纸摸了摸,里头那张五十两银票的硬挺轮廓还在。她把信封在手里转了两圈,嘴角反而牵起一点弧度。
“有点意思。”她说,“找工干,说明缺钱。但不要白给的钱,说明有骨气,有自己那套规矩。这种人最难搞,油盐不进。可一旦搞定了,比那些拿钱办事的牢靠十倍。”
汤闻骞给自己倒了杯茶,灌下去半杯,抹了把嘴:“说得倒是在理,可你打算怎么搞定?”
龙娶莹没理他的酸话,问:“你那边查得怎么样?”
汤闻骞放下杯子,拿起筷子夹了块酱牛肉扔嘴里,边嚼边说:“说实话,要不是这人麻烦事一堆,他还真是你要的天选之人——武功、身板、那股子狠劲,样样都对路。”
他顿了顿,筷子在盘沿敲了敲:“丞衍,二十五,外地人,具体哪村的说不清了。二十年前,凤河出过一桩‘大逆案’——现在没什么人提了,当时可闹得不小。”
“大逆案?”龙娶莹挑眉。
“听着邪乎。”汤闻骞又夹了片牛肉,“当时有个姓胡的绸缎商,儿子得了怪病,眼看不行了。不知从哪儿请来个道士,说要想续命,得把他儿子的‘面相特征’刮掉——就是脸上那点皮肉。光刮自己儿子还不够,得再找几个同岁的孩子,照着样一起刮。这么一来,阎王爷来勾魂的时候,就分不清谁是谁,可能就勾错了,把他儿子漏过去。”
龙娶莹听着,脸上没什么表情,只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
“丞衍那会儿大概四五岁,没爹没娘,吃百家饭长大的。”汤闻骞继续说,“村里人贪胡商人给的二十两银子,就把他卖了。结果刮到一半——胡商人那儿子自己咽气了。得,白忙活。几个孩子扔在胡家后院,没人管,后来还是衙门的人发现,送回去了。脸已经毁了,胡家赔了点汤药钱,这事就不了了之。”
龙娶莹拿起桌上那张画像,又看了看。画像上那完好的半边脸,眉骨挺拔,鼻梁笔直,要是没毁,该是副英气长相。
“可惜了。”她说。
汤闻骞“啧”了一声,放下筷子,开始剥虾:“可惜的还在后头。就前两年,县令公子赵志在城外河边,差点把个浣衣的姑娘给祸害了。正好丞衍路过,把人揍了一顿——没下死手,但揍得不轻。赵志记恨上了,回头就编了个故事,说丞衍跟衙门师爷新纳的小妾有染,还‘捉奸在床’。”
他剥出虾肉,蘸了蘸醋:“而衙门那帮人,谁敢驳县太爷公子的面子?当天就把丞衍锁了,游街示众。锣敲得震天响,满城的人都出来看热闹,指指点点,说什么的都有。后来那浣衣的姑娘,怕赵志报复,也怕自己名声坏了嫁不出去,转头就改了口,说是丞衍想欺辱她,赵志是去救人的。”
虾肉扔进嘴里,汤闻骞嚼了几下,摇摇头:“就这么着,丞衍的脸,算是彻底‘没’了。赵志还不罢休,这三年里,丞衍找什么工,赵志就派人去打招呼——谁敢用他,就是跟县太爷过不去。所以他才穷到要卖家传的刀。”
龙娶莹听完,手指在画像边缘轻轻摩挲,嘴角那点弧度慢慢扬了起来。
“就是他了。”她说。
汤闻骞一愣:“你刚才不还说这种人难搞?”
“难搞,才值得搞。”龙娶莹把画像放下,“你先让你手下的人去接触他,不必直接拉拢,就给他‘展示’一下咱们这条路——让他知道,有这么一个能来快钱、能翻身的法子,虽然要干的是杀头的买卖。”
汤闻骞皱眉:“你不是说他肯定不会干滥杀无辜的事?”
“所以不能直接让他干。”龙娶莹说,“先让他知道有这条路存在,然后……把他现在走的路,一条条堵死。人到了绝路上,看见什么都会想抓一把。”
她顿了顿,补了一句:“不要钱,不要施舍,那就只能让他信命了——信他自己的命,就是这么个走投无路的命。”
事情按龙娶莹说的往下走。
丞衍在集市上摆摊卖刀,摆了三天,问的人多,真掏钱的没有。他那张脸太吓人,加上赵志有意无意散播的“恶名”,寻常百姓不敢沾,有点见识的又嫌他开价高——十两银子,够普通人家过半年了。
第四天头上,龙娶莹亲自去了。
她换了身不起眼的灰布衣裳,头发束成男子式样。集市上人挤人,卖菜的、卖布的、卖牲口的,吆喝声此起彼伏。丞衍站在一个卖竹编的摊子旁边,戴着斗笠,帽檐压得很低,但那身量实在藏不住——肩膀宽,腰背直,站在人群里像根戳出来的柱子。
龙娶莹走近了,先看刀。
那把刀躺在粗麻布上,刀鞘是乌木的,已经磨得发亮,鞘口镶着一圈暗铜。刀柄缠着陈旧的黑色皮革,尾端嵌了颗不大的绿松石。她蹲下身,没碰刀,只是看。
“这刀不错。”她开口,声音压低了些,听着像个少年。
丞衍没动,只从斗笠下传来一句:“十两。”
旁边几个看热闹的凑过来,有个瘦老头咂嘴:“十两?小伙子,你这刀是好刀,可十两也太贵了。铁匠铺新打的,三两银子顶天了。”
另一个矮胖的中年人帮腔:“就是,这刀鞘都旧成这样了。”
龙娶莹没理他们,伸手——没拔刀,只是用手指在刀鞘上轻轻叩了两下,侧耳听那声音。然后她抬起眼,看向丞衍:“十两?你这刀卖贱了。”
周围人都一愣。
瘦老头“嘿”了一声:“小兄弟,你可别瞎说,这刀哪儿值十两?”
龙娶莹不急不慌,手指虚点:“看鞘口这圈铜,不是寻常黄铜,是掺了锡的‘响铜’,敲击声脆,能镇邪——这是军器监早年给将官佩刀用的规制。再看刀柄缠皮,是水牛皮浸桐油反复捶打出来的,防水防滑,能用几十年不烂。尾端这颗石头,看着不起眼,是绿松石里的‘天蓝料’,产自西域,一般只镶在五品以上武官的刀上。”
她顿了顿,抬头看丞衍:“这刀,要么是军中将官的家传物,要么是武库流出来的好东西。十两?拿去当铺,当死当也能当十五两。你这价,开低了。”
周围人听得一愣一愣的,有信的,有不信的,都小声嘀咕起来。有人觉得龙娶莹是懂行的,也有人觉得她是个托,故意抬价。
丞衍终于动了动。他微微抬起头,斗笠下那完好的半边脸露出来一点,眼睛看向龙娶莹。那眼神很静,没什么情绪,像深潭水。
就在这时,集市东头忽然传来一阵骚动。
有人骂骂咧咧的声音由远及近,听着就不是善茬。人群像被棍子拨开的水,自动往两边分。十几个穿着青灰色短打、腰别短棍的汉子拥着一个人走过来——为首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,穿着绸缎袍子,脸上挂着笑,可那笑里带着股狠劲。
正是赵志。
周围摆摊的、买东西的,一见这阵仗,都低下头,往后退,生怕沾上。卖竹编的摊主赶紧把摊子往后拖,菜贩子把菜筐往怀里拢。
丞衍显然也不想惹事。他收起刀,用麻布裹好,转身就要走。
“哎——别走啊。”赵志开口了,声音拖得长长的。他身后那十几个汉子立刻散开,成一个半圆,把丞衍围在中间。
赵志背着手走过去,他个子不矮,但只到丞衍肩膀,得仰着头看人。但他架势足,指着丞衍怀里裹刀的麻布:“我听说,有人在这儿卖假刀,骗咱们凤河老百姓的钱?”
丞衍没说话,只是把刀抱紧了些。
“怎么,心虚了?”赵志伸手就去扯那麻布。丞衍侧身躲,赵志抓了个空,脸上挂不住,朝手下使了个眼色。两个汉子立刻上前,一左一右去夺刀。
丞衍不想动手,只是护着刀往后退。但对方人多,推搡间,不知谁撞了他一下,斗笠掉了。
那张脸露出来一半——完好的半边英挺,毁掉的半边狰狞。周围响起一片抽气声,有人低声惊呼,有人别过头不敢看。
丞衍立刻抬手捂住脸,头低下去,背脊却绷得笔直。
赵志看见他这反应,笑得更大声了:“遮什么遮?长成这样,出来吓人还有理了?”他一步上前,这次直接抓住了刀鞘,用力一扯,“我看看,到底是什么破铜烂铁,敢要十两!”
丞衍还是没松手。两人就这么拽着一把刀,僵在那儿。
赵志脸上有点挂不住了,他朝手下吼:“都愣着干什么?给我抢过来!”
几个汉子一拥而上。混乱中,不知谁踩了谁的脚,谁又推了谁的背。龙娶莹站在人群外围,眼睛扫过混乱的中心,又往斜后方瞥了一眼——汤闻骞手下那个精瘦的汉子正混在人群里,慢慢往前挤。
就在赵志第二次发力夺刀的瞬间,那精瘦汉子恰好挤到他身后,脚下一绊——看着像是被人群挤的,不稳。
赵志整个人往前扑去。他手里还拽着刀鞘,这一扑,刀“锵”一声被拔出半截。丞衍下意识往回抽,赵志却已经收不住势,胸口直直撞上那出鞘的刀刃。
时间好像顿了一下。
赵志低头,看着插进自己肚子里的刀,脸上那点嚣张的笑还没完全褪去,就变成了茫然。他张了张嘴,想说什么,却没发出声音,只是手指颤抖着指向丞衍。
丞衍也愣住了。他握着刀柄的手僵着,血顺着刀槽往下淌,滴在尘土里。
周围死寂了一瞬。
然后汤闻骞安排在人群里的人尖声喊起来:“杀人了——!丞衍杀人了——!”
像往滚油里泼了瓢水,人群“轰”地炸开。尖叫的,推搡的,往远处跑的,乱成一团。赵志手下那帮汉子也慌了神,有去扶赵志的,有想去抓丞衍的。
丞衍猛地抽出刀,血喷出来,溅了他一手。他看了眼手里的刀,又看了眼倒在地上的赵志,脸色煞白。下一秒,他转身就冲开人群,往集市外头跑。
龙娶莹站在原地没动。她看着丞衍逃走的背影,又看了眼地上被人围住的赵志,转身,逆着慌乱的人流,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汤闻骞那个精瘦汉子悄无声息地跟了上来。
“人跟上去了?”龙娶莹问,声音平静。
“跟着了,跑不了。”汉子答。
“赵志呢?”
“抬去济世堂了,看样子伤得不轻,但未必会死。”
龙娶莹点点头:“走,去济世堂。”
济世堂是凤河最大的医馆,坐落在城东。龙娶莹到的时候,门口已经围了不少人,都是跟着看热闹的。赵志被抬进内堂,门关着,里头传来大夫急促的吩咐声和小吏跑动的脚步声。
龙娶莹没往里挤,只站在街对面一个卖糖人的摊子旁边,像寻常看客。汤闻骞那个手下不知何时也来了,低声说:“咱们的人混进去了,是个学徒,专门递纱布和热水的。”
约莫过了半个时辰,内堂的门开了条缝,一个学徒探出头,朝外头喊:“血暂时止住了,但伤得深,得用人参吊气!快去库房取那支老山参!”
门外守着的一个家丁模样的人应了声,匆匆往后院跑。
龙娶莹朝手下使了个眼色。
那汉子会意,悄无声息地绕到医馆侧面,从一扇半开的窗户翻了进去。
又过了一炷香时间,内堂突然传来一声变了调的惊呼,接着是东西摔碎的声音。门被猛地拉开,刚才那学徒连滚带爬跑出来,脸白得像纸:“没……没气了!赵公子没气了!”
人群哗然。
龙娶莹转身,离开了济世堂门口。走出一段,汤闻骞那手下跟上来,低声说:“办妥了。伤口本来已经裹好,我趁乱在包扎的棉垫底下,又按进去一根浸过药的针,顺着原来的伤口刺进去三分。外头看不出来,但内里出血止不住。”
“针呢?”
“留在里头了,裹在血肉里,除非剖开验尸,否则发现不了。”
龙娶莹点点头,没再多问。
傍晚时分,凤河县衙出了海捕文书,贴得到处都是——上头画着丞衍的像。文书上说,恶徒丞衍当街行凶,杀害县令公子赵志,罪大恶极,悬赏一百两捉拿。
龙娶莹站在一张告示前看了会儿,转身回了宅院。
汤闻骞已经在屋里等着,见她进来,倒了杯茶推过去:“这下,咱们的‘萨拉’,算是彻底没退路了。”
龙娶莹接过茶,没喝,只是捧着暖手。
窗外天色渐暗,凤河城的灯火一盏盏亮起来,看似太平的夜晚底下,有什么东西已经搅动起来了。
她想起丞衍逃跑时那个仓皇的背影,又想起赵志临死前茫然的眼神。
“路是人走出来的,”她轻声说,像对自己说,又像对看不见的什么人,“退路没了,就只能往前走了。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